尹韻公:《新青年》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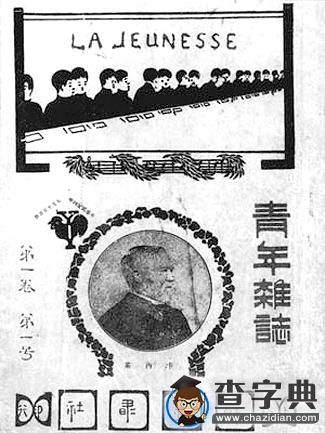
《青年雜志》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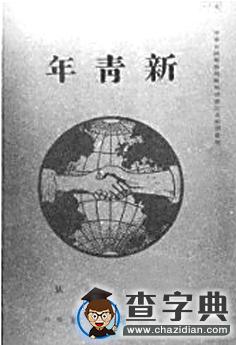
《新青年》第八卷一號
根據史料記載,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報刊,應是1889年4月的《萬國公報》,該報在介紹西方各種政治倫理學說時,不經意地提到過馬克思學說。之后,1903年第8期的《浙江潮》和1906年第2、3、4號的《民報》都分別零星、碎片式地介紹了馬克思學說的一些觀點和主張。
而真正在中國大力宣傳和強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報刊,當屬《新青年》,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我們又要看到,作為當時思想最激進和最先進的《新青年》,在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也走過曲折的歷程。《新青年》起初名為《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創辦于1915年9月15日。在該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了陳獨秀撰寫的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文中論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度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
該文又說:“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壞無余,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毋庸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可謂之反對近世文明之歐羅巴。最近文明說始于法蘭西革命時,有巴布夫者,主張廢棄所有權,行財產共有制。其說未為當世所重。19世紀之初,此主張復盛興于法蘭西,圣西孟及傅里耶,其最著稱者也。彼等所主張者,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才能以事事,各稱其勞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而建設一新社會也。其后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及馬克思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甚,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歐洲社會岌岌不可終日,財產私有制雖不克因之遽廢,然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于貧困之度過差,絕非社會之福,于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制兼并,所謂社會政策是也。晚近經濟學說,莫不以生產分配相提并論,繼此以往,貧民生計或以昭蘇,此人類之幸福。”
從以上論述看,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源和主要思想,是相當熟悉和基本把握的。但是,從認識層面上講,陳獨秀在1915年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還是淺層次的,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廣泛介紹西方的政治學說、文藝學說、教育學說和科學精神等,從而幫助中華民族從西方思想庫中選擇一件或幾件可用和有用的思想武器,馬克思學說和社會主義只是其中之一。陳獨秀不僅介紹各種社會思潮,而且還廣泛介紹西方杰出人物,如卡內基、托爾斯泰、叔本華、富蘭克林、興登堡元帥、霞飛將軍等,然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卻一個未見。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通信”欄目上,刊登了一位名叫褚葆衡的讀者來信。信中說:“屢讀大志,欽佩無似。際茲公理消沉、邪說橫行之時,貴報乃能獨排眾議,力挽狂瀾,誠足稱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燈光也。”“貴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諦,多所輸入,實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對孔教,尤能發揚至理,足使一般中國國教之迷者,作當頭棒喝也。近代文明之真諦,最新之思潮,仆以為當推社會主義。此種學說,當政府及資本家專橫之反應,大足為我人研究之資料。我國于此種主義輸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強權者勢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貴報素主輸入世界新理,獨于斯類學說乃未多講。足下如以社會主義實可為救世之良藥,則闡揚之責,端在貴報矣。仆愿望如此,不識足下以為如何。”
可以看出,這位讀者極為推崇社會主義,也期待《新青年》大力闡揚社會主義。對此,《新青年》以記者名義答復道:“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因產業未興,兼并未盛行也。”這位記者是誰,無法確認,但這個答復至少得到了陳獨秀的認可,也反映出了陳獨秀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程度是有限的。
毛澤東曾說過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當說,毛澤東的表述極為準確。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炮響,雖然沒有一下子驚醒或震醒中國人,但畢竟讓中國人比較快地知道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和11月17日長沙《大公報》都報道了俄國政權更迭的消息,但均被埋沒在當時更大的戰事報道之中。毛澤東何時知道十月革命的,史無確載。據《毛澤東年譜》稱:毛澤東是1918年8月19日因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到達北京的。在北京大學,毛澤東開始接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書刊。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熱烈贊揚十月革命,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時隔一年,十月革命的價值和意義,才真正為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所掌握。
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和第六期集中版面,組織力量,猛烈宣傳馬克思主義,相繼刊發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馬克思學說》《馬克思學說批評》《馬克思研究》《馬克思傳略》等文章,全面、深入、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主要觀點。從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結束了在中國空中飄蕩不定的狀態而最終在中國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漸開花結果。由此可見,《新青年》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功不可沒,《新青年》為中華民族選擇了最好的思想武器,功不可沒。
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發行《勞動節紀念》專號。這就有力表明,《新青年》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把握上,達到了新的歷史自覺高度,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里程碑。在當時有影響的國內報刊中,唯獨《新青年》把自己的重大關注投給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個了不起的行為宣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由此開始了它那偉大而艱辛的歷史起步。
同年9月,中共上海發起組決定,從第八卷起,將《新青年》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的封面設計很好地體現了全新的編輯意圖:封面正中是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個半球伸出兩只有力的手,緊緊相握。《新青年》編作者之一、著名作家茅盾曾經這樣解釋圖案設計用意,說:“這暗示中國人民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密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四輯)在這一期,陳獨秀發表了《讀政治》一文,宣稱:拋棄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從文人學者轉為馬克思主義信徒——從淺信到深信,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經典標本。他的言行給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他引發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立場轉變,在老一輩革命家和著名文人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找到太多的鮮活例證。例如,毛澤東在北京接受馬克思主義熏陶后,1919年回到湖南也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在同年7月創辦的《湘江評論》中連發《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熱情稱頌俄國的十月革命勝利,強調改造國家、改造社會。
必須指出,1919年發生的著名的“五四運動”也大大提高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如果說,十月革命的勝利,激發了中國知識界精英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五四運動”的爆發,則為馬克思主義在一般民眾的大面積傳播,準備了很好的氛圍和前提條件。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



